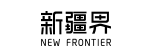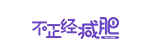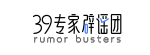摘要:创伤后成长是指在与生活中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许多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创伤事件的特征、人格与认知、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等都对创伤后成长有影响。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未有一致的结论,两者间关系的不一致有四种可能的解释。未来研究应注意创伤后成长与相关概念的区别,探寻确证成长有效性的新证据和新方法。
关键词:成长;创伤;创伤后成长
分类号:R395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上》)孩提时代耳熟能详的经句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苦难和挫折暗含着成长和成功的可能。一直以来。有关创伤后心理机制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创伤事件引发的负性结果,但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创伤后成长在近十几年内受到了学者们的积极关注(Helgeson,Reynolds,& Tomieh,2006)。创伤后成长强调创伤后个体自我恢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它的提出将一改心理病理领域一直以缺陷为基础的研究预设,对该现象的深入研究能增进对创伤后心理机制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将为临床上如何更有效地激发成长以及恢复和提升创伤者的身心机能提供有益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将引入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围绕该概念在相关研究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论述。
1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
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Tedeschi等人就对个体能从创伤等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成长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但在对该现象的正式测量中才首次正式提出并使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growth.PTG)一词fredesehi&Calhoun,1996),并将其界定为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Tedeschi&Calhoun,2004)。创伤后成长不仅能发生在个体水平上,它也能发生在群体或国家,甚至世界水平上,历经压力或创伤能使婚姻关系、家庭机能、邻里关系、组织士气发生变化,甚至能使一国和一地区内产生社会变革和文化变动(Cohen,Cimbolic,Armeli,&Healer,1998)。我们可以想象,在历经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后,人们的团体凝聚力会增强,慈善或正义的行为会增多。除创伤后成长外,指代该现象的词语还有很多,如与压力相关的成长(stress-related growth)、益处寻求(benefit-finding)、感知到的益处(perceived benefit)、观念的变化(changes in outlook)及心理活力(psychological thriving)等(Linley&Joseph,2004),而Joseph和Linley(2006)则提出用逆境与成长(growth following adversity)一词来统指上述各称谓。但Tedeschi和Calhoun给出了之所以选择使用创伤后成长一词的充分理由,他们认为该词不但抓住了成长的本质,而且和与压力相关的成长相比,它突出强调,了引发成长的事件的危机性、挑战性和威胁性;与积极幻想和心理活力相比,它反映了人们在创伤后表现出实际的成长以及成长与心理痛苦(psychological distress)共存的事实:而与将成长看作应对策略的观点相比,它表明成长是创伤后的结果或适应过程。因此,本文如不作特别说明,仍用创伤后成长来指称成长,但所引文献中已有的用以指称成长的各个词语仍予以保留而不作改动。
引发创伤后成长的事件和成长的领域都有很多。引发创伤后成长的事件主要包括丧失亲人、意外事故、自然灾害、心脏病发作(heart attacks)、战争或政治迫害、性虐待和强奸以及各类疾病,如SARS、HIV/AIDS、脑损伤和癌症等。但与其它类型疾病相比,癌症具有许多独特性(Mehnert&Koch,2007)。而创伤后成长的领域主要有觉知到的自我、人际关系和生活哲理方面的变化(Tedeschi&Calhoun,1996),还包括物质获得、娱乐价值、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现、工作条件改善及法律政策的改变(McMillen&Fishea 1998)以及对他人同情和信任的增强、助人能力的提升、更为成熟地处理将至的创伤、加深对自我的认识、终止酒精与毒品伤害以及邻里之间的互助合作等(McMillen,2004)。对特定创伤所做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成长领域,如儿童期受到性虐待的成年被试,其创伤后获益体现在保护小孩免受虐待、自我保护、儿童性虐待知识的增加以及更为坚强的人格品质等方面(McMillen.Zuravin,&Rideout,1995)。尽管成长的领域有许多,但有研究发现,各成长测量工具的各个子量表共享一个高阶因素,这似乎表明成长的多个领域或维度可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fJoseph.Linley,&Harris,2005),成长领域或范围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可能反映了事件类型、发生时间及人格等因素的作用(cohen,Hettler,&Pane.1998)。
与创伤后成长相关的概念有很多,如韧性(resilience)、坚韧(hardiness)、乐观、凝聚感(sense of coherence)、寻求意义(making sense)等。除韧性外,这些概念往往被研究者们直接当成与成长相对的不同概念,但许多研究者或明或暗地将创伤后成长与韧性等同了起来。其实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是指尽管面临人生的丧失,困难或身处逆境,但仍然能够有效地应对和适应(Yu&Zhang,2007,),而创伤后成长则指挫折后人的身心机能不但能有效地应对和恢复,而且还能有所提升。当面临挫折时,人的心理机能水平可能反弹至原先的水平,也即韧性,但也可能机能水平不但反弹至原先的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越先前的水平,也即表现为成长(Linley&Joseph,2005)。相比较而言,尽管韧性一词也包含有成长之意,但创伤后成长则明确提出并强调韧性中的成长,实证研究也初步证明韧性与创伤后成长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事物(Westphal&Bonanno.2007)。
2 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
2.1人口统计学变量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得分更高(Aslikesimci&Tulin,2005;Park,Cohen,&Murch,1996),Polatinsky和Esorev(2000)对失去小孩的父母亲所做的比较却发现,父母亲在获益上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因样本量较小,有可能检测不出差异。被试年龄越小,其在益处寻求量表上的得分会越高(Lechner a1..
2003)。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所体验到的刨伤后成长有下降的趋势(Jaarsma,Pool,Sanderman.&Ranchor,2006)。少数民族身份是唯一可以预测成长中新的可能性的因素(Maguen,Vogt,King,L.A.,King,D.W,&Litz,2006),而且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能从创伤事件中获得更多的益处(siegel,Schrimshaw,&Pretter,2005)。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及受雇佣情况对创伤后成长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Bellizzi&Blank.2006)。
除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外,文化与宗教信仰对创伤后成长也有影响。研究发现,信仰改变的开放度与创伤后成长有高的正相关(calhoun.Cann,Tedeschi,&McMillan,2000),精神性(spirituality)也与成长有显著的正相关(Cadell.Regdhr,&Hemsworth,2003)。不但如此,具有宗教性质的应对方式也与益处寻求有密切关系(Proeeitt,Cann,Calhoun,&Tedeschi.2007;Urcuyo,Boyers,Carver,&Antoni,2005)。另外,对历经恐怖事件的青少年所作的研究也发现,与没有宗教信仰的青少年相比,那些有宗教信仰者报告发生了更多的成长(Laufer&Solomon.2006)。Shaw,Joseph和Linley(2005)在对lI篇有关宗教信仰(religion)、精神性及创伤后成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后认为:宗教信仰和精神性通常对那些正在应付创伤者有助益:创伤体验能导致对宗教和精神性的信赖加深;积极的宗教应对、信仰的开放性、面对存在性问题的隹备性(readiness to face existential questions)、宗改参与及发自内心的对宗教的虔诚(intrinsicreligiousnessl等因素通常都与成长相关联。最后,有证据表明成长的领域及内容具有文化差异性。Shakespeare-Finch和Copping(2006)用扎根理论对澳大利亚成人所做的研究,并未发现精神或信仰因素的存在,而且精神性(spirituality)、宗教信仰和同情的内涵也与美国文化不同。而Samuel,Cecilia和Rainbow(2004)对中国香港188名成年癌症患者所做的研究也发现,考虑文化因素后的人际间一人际内两因素模型能比较好地拟合数据。
2.2创伤事件的特征
(1)严重程度。那些评估事件具有中等程度以上的威胁以及适度挑战性和严重性的被试,其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的得分更高(Armeli,Gunthert,&Cohen,2001)。就可控事件而言,对不可控事件采取情绪中心的应对方式将导致更多的成长(Goral,Kesimci,&Gencoz,2006)。感知到事件的威胁程度对创伤后成长的三个维度都具有显著预测作用(Maguen,et a1.,2006),但癌症的客观严重程度却与创伤后成长无关(Barakat,Alderfer,&Kazak,2006)。另外,创伤后成长与事件的严重程度可能并非为学者们早先所认为的那样。是直线关系,而实质上也可能曲线关系。譬如,与处于不太严重或非常严重程度的癌症患者相比,处于中等严重程度癌症患者报告了更多的益处寻求fLechner,et a1.,2003.),之所以如此,Tomich和Helgeson(2004)推测认为,疾病太过于严重可能完全耗尽创伤后成长赖以成长的心理资源,而太轻的疾病却不足以对创伤历经者的认知图式等产生震撼性的影响,因此成长都不易发生。(2)类型。研究发现被试感知到的益处在事件类型上有差异。譬如,与面临工作压力的人相比,那些面临所爱之人死亡的人在对人同情方面的得分就更高(McMillen&Fisher,1998),,而与飞机失事的幸存者相比,历经龙卷风灾难的人在亲密感和个人力量方面有最大的获益(MeMillen,Smith.&Fisher,1997)。另外一项为期18个月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在控制创伤前的心理痛苦程度后,事件类型仍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的不同组合间有关系(Ickovics,et a1.,2006)。但也有研究发现,被试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的得分在事件类型上无显著差异(Park,et a1.,1996)。各研究间之所以出现差异,可能是因为事件本身的差异程度不够大或者不具有质的差异;事件类型本身对创伤后成长无直接影响,需要通过当事人对所发生事件的认知、情感评估才能发生作用。(3)发生时间。发生时间是指创伤事件发生时或被诊断出患有某疾病时离成长测量时的时间跨度。一些研究表明成长与创伤事件的发生时间无关(Park,et a1..1996;Tedeschi&Calhoun,1996),Stanton,Bower和Low(2006)也认为,从现有研究来看,我们无法确知发生时间是否与成长有关,但Zoellner和Maereker(2006)认为,成长的发生是需要时间的,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伤后成长的积极面才能显现出长期的适应价值。
2.3 人格、认知变量
成长与大五的神经质无显著相关,但与大五的其余四个维度及乐观均显著正相关(Park,et a1.,1996;Zoellner,Rabe,Karl,&Maercker,2008),但也有研究发现乐观与创伤后成长的任何子维度均无关。并且不能有效预测成长(Bellizzi&Blank,2006)。研究发现,对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所做的归因能够有效预测病人8年内的死亡率(Ameek,Tennen,Croog,&Levine,1987),而与那些做外在、特定和不稳定归因的被试相比,对正性事件做稳定、广泛和内在归因的被试报告了更多的成长(Samuel,Kwung,&Jessie,2008)。除归因方式外,自我效能感、自尊等也对成长有影响。自我效能感对生活不完美的接纳度等多个成长领域有直接影响(Luszezynska,Mohamed,&Schwarzer,2005).而自尊对心理活力有直接作用(Abraido-Lanza,Guier,&Colon,1998)。高自尊的高乐观者会报告更多的成长(Evers et a1.,2001)。另外,韧性(resilience)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而且是创伤后成长唯一的预测变量(Hooper,Marotta,&Lanthier 2008),创伤后成长也与感知到的积极品质(pereeived positive attributes)的变化显著相关(Ransom,Sheldon,&Jacobsen,2008)。
事发后旋即发生的沉思(rumination soon
after the event)程度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Taku.Calhoun,Caun,&Tedeschi,2008)’而且对事件的认知加工深度也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Weinrib,Rothrock,Johnsen,&Lutgendorf2006)。纵向研究发现,成长与生活意义(lifemeaningfulness)在两个不同时间点上均显著相关(Park.Edmondson。Fenster,&Blank,2008)。另外,对矿难者伴侣所做的质性分析也发现,获得个人成长者,往往感知到事件对自我的威胁,并从创伤中找寻到了意义,而那些未获成长者,往往不能从创伤中发现意义(Davis,Wohl,&Verberg.2007)。除上述因素外,目标的性质与创伤后成长也有关。创伤后成长与内源性目标和外生性目标间相对重要性的变化相关联,表现为内源性目标变得更为重要(Ransom et a1.,2008)。最后。历经创伤并获成长者,将获得苦难人生的回报——智慧(wisdom),它能通过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与管理等三个维度来激发创伤后成长(Linley,2003)。
2.4 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
实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一发现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Karanci & Erkam.2007;Schwarzer,Luszezynska,Boehmer Taubert,&Knoll,2006),不仅如此,感知到的支持对成长也有促进作用。Weiss(2004)研究发现,仅感知得到丈夫的支持,患癌症的妻子都会报告出更多的成长,而与那些体验到成长的癌症幸存者有简单接触的被试相比,那些未有接触者会报告更少的成长。另外,来自重要他人(如伴侣)对疾病的认知和情感因素与患者本人的创伤后成长也显著相关(Manne eta1.,2004),哪怕仅有来自朋友的支持也能对创伤后成长有所助益(Lev-Wiesel&Amir.2003)。Leehner和Antoni(2004)认为,由社会支持构筑而成的团体环境是创伤后成长得以发生、发展的土壤,因为它为创伤经历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观点、获得新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共享创伤体验的平台,而这些都有利于当事人认知图式的重构和适应。
研究发现,使用问题导向和宿命应对策略(fatalistic coping strategies)频率越多者,其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量表上得分越高(Aslikesimci&rulin,2005,),而具有积极性质的应对方式也与创伤后成长的多个维度有高的正相关并能显著预测成长(Bellizzi&Blank,2006)。另外,情绪中心的应对策略也能导致更高水平的与压力相关的戎长(Goral et aI.,2006)。研究还发现,创伤后成长的领域与应对机制密切相关,也即不同成长领域与不同的应对机制相关(Morris,Shakespeare。?inch,&ScoR,2007)。另外几项纵向研究还发现,研究开始时的积极重评策略能够有效预测12个月时的创伤后成长(sears,Stanton,&Danoff-Burg 2003),而在骨髓移植前,那些使用积极重评等应对方式的被试会报告出更多的创伤后成长(Widows,Jacobsen,Booth-Jones,&Fields.2005)。
最后,除上述因素外,研究也发现情绪对创伤后成长有影响。正性情绪对心理活力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而负性情绪则通过自尊对心理活力产生间接作用(Abraido-Lanza et a1.,1998),在间隔9个月的三个时间点上,情绪表达和情绪加工对患者本人及其伴侣的创伤后成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Manne et a1.,2004),与那些低正性情绪、高负性情绪以及正负性情绪都低的人相比,那些具有高正性情绪和低负性情绪者,具有最高水平的能从创伤中获得活力(thriving)的能力(Norlander,Sehedvin,&Archer,2005),手术后幸存者在手术前的负性情绪对1年后的创伤后成长水平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Thornton&Perez.2006)。
综上所述,对创伤性事件的认知评估而非客观的严重程度是创伤后成长发生的重要条件,但两者到底为何种关系仍不清楚。时间长短并非表征创伤后成长发生过程的有效指标,因为现有的横断研究混淆了时间与创伤后成长的积极成分和幻想成分间的关系。总的看来,在乐观、韧性、自我效能、自尊、外倾与开放性上得高分并作稳定、广泛和内在归因的那些非白人的年轻女性.当其认为创伤事件非常具有挑战性和震撼性,对该事件进行深层次的认知加工和积极沉思,并采用了适应良好的应对策略,在有重要他人实际提供的或自己感知到的支持下,更易报告发生了成长,并且具有更高的创伤后自我恢复和发展的潜能以及对创伤更强的抵抗力,创伤后也有更高的身心机能、心理健康、幸福水平和更低的心理痛苦感水平。另外,正性情绪对成长有正向的助益作用,而负性情绪对成长的作用则不明确,其作用机制可能受到创伤事件发生的时间、对创伤事件的认知评估及应对策略的调节。
3 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成长与适应良好和高健康水平有关。从横断研究来看,成长与抑郁显著负相关(siegel et a1.,2005),与情绪上的痛苦(emotional distress)负相关(Urcuyo et a1.,2005).与适应水平正相关(MeCausland&Pakenham,2003)。从纵向研究来看,与压力相关的成长能有效预测6个月后的积极心理状态(Park & Fenster,2004),益处寻求对表征积极结果的一些心理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绪和动态调适,均具有强的直接作用(Pakenham,2005),而人际关系方面的获益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残疾程度及心理痛苦程度显著负相关,并且获益组的心理痛苦程度显著低于无人际关系获益组(Danoff-Burg&Revenson,2005),在术前1周及术后1个月和12个月的三个时间点上,益处寻求在前两个时间点上的变化能够显著预测第3个时间点上的抑郁、生活质量及对健康的担心水平(Schwarzer et a1.,2006)。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的恶化无关或正相关。研究发现益处寻求与抑郁无关,与高焦虑和高愤怒水平有关(MohL Dick,Russo,Likosky,&Goodkin,1999),先天脑损伤病人的焦虑和抑郁得分与创伤后成长显著正相关(Mcgrath&Linley,2006)。而乳腺癌幸存者在创伤后成长上的得分与在抑郁自评量表(cES-D)和gyff心理幸福感量表(Ryff's
Well-Being Scales)上的得分也无关(cordova,Cunningham,Carison,&Andrykowski,2001,),与生活质量也无关(Thomton&Perez,2006)。研究甚至还发现,目睹一系列恐怖和暴力事件的被试,其创伤后成长与更高水平的心理痛苦相关(Hobfoll et a1.,2007)。
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间关系的不一致,有许多可能的解释:其一,创伤后成长与心理健康的恶化间的无关或正相关,反映了创伤后成长能与心理痛苦共存这一事实。譬如,那些历经丧子之痛的父母会在好些年里频频报告其体验到的痛苦.但同时也会报告体验到了创伤带来的成长(Tedischi&Calhoun,2004)。其二,各研究大多以成长和表征心理健康各指标的总分作为分析单元,这既掩盖了创伤后成长的多领域性以及各个成长领域自身发生发展的特殊性,也会使数据分析发现不了某一具体的成长领域与心理健康某一子指标间的关系情形;其三,成长与心理健康可能并非如大多数研究者所预设的那样,是线性关系,而可能是曲线关系。对两个乳腺癌患者样本在术后1年及术后5-8年的追踪研究就发现,与益处寻求处于中间组的被试相比,高低益处寻求组均有更好的适应(Lechner Carver,Antoni,Weaver & Phillips,2006)。其四,有许多研究表明,成长与心理健康要受到认知等许多变量的调节。创伤发生的平均时间、研究中是否使用特定的测量工具、样本中少数民族被试所占的比例(Helgeson et a1.,2006)、癌症等疾病所处的发生阶段(Tomich&Helgeson,2004)以及乐观和正性情绪(Cordova et a1.,2001)都对成长与心理健康各变量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4 研究展望
对创伤后成长本质的进一步探究亟待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指称同一现象的不同称谓是否真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从现有研究来看,对癌症等疾病加以研究的学者大多采用益处寻求,而对丧失亲友、自然灾难和偶发事件的研究,则大多采用创伤后成长,而有关校园压力等的研究,则更多采用的是与压力相关的成长,这到底反映的仅是各研究者在学术背景、研究领域和使用偏好上的差异,还是暗藏着内涵和本质的不同呢?有研究发现,益处寻求、创伤后成长与积极重评这三者间尽管紧密相关,但却可能是不同的结构(Sear et a1.。2003)。另外,未来研究还须注意弄清创伤后成长与韧性、坚韧、乐观及凝聚感等概念的区别(Tedeschi&CMhoun,2004)。第二,引发创伤后成长的事件非得具有危机性和挑战性吗?从现有研究来看,激发成长发生的事件既可能是非常严重的身体疾病,也可能是相对轻微的压力事件,还可能是自然灾害、战争和交通事故,甚至也可以是因见证别人的疾病而带来的替代的痛苦体验(cadell,2007)。既然成长是个体主观感知到的(self-perceived posttraumatie growth)(Zoellner&Maercker,2006),那么符合逻辑的推论是,任何一件事件,无论严重程度如何,都有可能令被试感知到成长,只要创伤信息与事发前个体所持的有关自我和世界观念(worldassumptions)不相符或相互冲突,并有可能动摇其事发前的假设,成长就可能发生(Joseph&Linley,2005)。第三,创伤后成长具有领域特定性吗?特定的成长领域是否与特定的创伤事件相关联,成长是否为具有整合性的单维结构,只要发生,就会显现在各个领域?还是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各个成长领域各有其不同发展趋势和规律,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心理健康有着各自不同的关系?第四,成长一定只有现实面,或只有幻想面吗?Taylor(1983)认为,积极幻想在成功应对创伤的过程中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个体从创伤中痊愈还有赖积极幻想。但创伤后成长肯定也不只是一种幻想(Tedeschi,Calhoun,&Cann,2007),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发生的事实(Sumalla,Ochoa,&Blanco,2009)。Zoellner等(2006)认为区分二者有赖于随时间的流逝,被试所使用的不同认知策略重要性的相对变化。第五,成长难道只是创伤后的结果吗?尽管从词面意思来看,创伤后成长一词表明成长是创伤后的结果,但不同研究者仍或者将其看成是创伤性后的结果,或者看作是一种应对策略,或者是一个过程(Maercker&Zoellner,2004)。
从研究方法来看,创伤后成长发生的时间需求特性要求未来更加侧重纵向追溯性的研究并采取更为巧妙的研究设计,如采用重要他人评定法,或使用控制分析法,或使用配对控制组法(cohen et a1.,1998),以及借鉴开放式访谈以及个人叙事等质性研究的结果,最为重要的是要采用重要他人外显行为测量法,以考查创伤后成长在个体行为层面的实际情形,因为毕竟只有基于信念的行动,才能有效克服有关成长仅是一种防御或幻想的猜测(Johnson et a1.,2007)。
创伤后成长这一概念本身就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认当事人自己就有从创伤和苦痛中自我恢复、痊愈和成长的力量,认为成长的激发有赖于个体自身内在的信念体系的改变。尽管有研究表明益处寻求与焦虑和广泛性痛苦(global distress)无关,与更低的抑郁和更高的幸福水平相关(Helgeson,Reynolds,&Tomieh,2006),但Joseph和Linley(2006)仍十分严肃地指出:将成长应用于临床应保持充分的谨慎,因为到目前为止,成长发生的内在机制仍不清楚,痛苦可能与成长并存,当痛苦结束时,成长也就可能终止了,这样一来,现有的立足于减轻当事人痛苦的治疗措施,反而会起到间接终止成长发生、发展的负向作用。因此,未来临床上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共同对创伤后成长起作用的途径、机制以,以及这许多因素与成长发生关系的具体情形,深入挖掘调节变量在成长与心理健康间起作用的内在机制,更要弄清成长积极面与幻想面的关系以及探寻如何区分二者的新方法和新证据。
(实习编辑:张欣)
39健康网(www.39.net)专稿,未经书面授权请勿转载。

 39健康网
39健康网 创伤一般由什么组成
创伤一般由什么组成 脑创伤后巅痫治疗方法有什么
脑创伤后巅痫治疗方法有什么 立足羊城、辐射湾区!广州启动烧伤创伤一体化救治体系建设
立足羊城、辐射湾区!广州启动烧伤创伤一体化救治体系建设 学习自救互救技能,30名小学生变身“应急小医生”
学习自救互救技能,30名小学生变身“应急小医生” 创伤梗塞是什么症状
创伤梗塞是什么症状 创伤是45岁以下人群第一死因!打造珠江创伤快速综合救治模式
创伤是45岁以下人群第一死因!打造珠江创伤快速综合救治模式 Neurology:轻度创伤性脑损伤 1 年后的认知结果:TRACK-TBI 研究的结果
Neurology:轻度创伤性脑损伤 1 年后的认知结果:TRACK-TBI 研究的结果 冷暴力和家暴哪个更可怕?有些时候冷暴力比家暴更恐怖
冷暴力和家暴哪个更可怕?有些时候冷暴力比家暴更恐怖 Psst!聊八卦还有这好处!
Psst!聊八卦还有这好处! 为什么!我!又走神了!
为什么!我!又走神了! 大脑爱“吃瓜”:记啥啥不行,八卦第一名
大脑爱“吃瓜”:记啥啥不行,八卦第一名